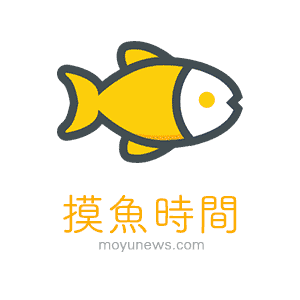我们之所以怀念80年代,是因为那是一场温柔的反叛。并不是创作者在反叛,而是阅读、聆听、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反叛。这种反叛,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反应,底层像岩浆一样涌动,上层内心依然烦乱。其实,对精神文明的宽松就是对老百姓的宽容。
這段時間,常常看到懷念80代的文章。
我想與其讓那些抄襲的人談80年代,還不如我自己來聊一聊那個時代。
實際上,80年代是個不成熟的時代,無論是社會建設、經濟還是文化,都無法與當下相比。但是,它年輕、真誠,富有朝氣,充溢著理想主義。而這些,如今離我們,已經越來越陌生。
01
70年代末、80年初,動亂已過,百廢待興。
當時還是造紙工人的芒克、建築工人的北島,在北京亮馬河小院,守著一臺借來的油印機,連幹三天三夜不休,創立詩刊《今天》。詩刊以地下小報形式,流傳大街小巷。眼神青澀的顧城,在上面發表了《一代人》:
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卻用它尋找光明!
在工廠焊燈泡的舒婷,讀到這首詩時,情緒悸動,說就像受到八級地震。
之後詩歌浪潮席捲全國,誕生詩社2000多家,流派88個。北島、芒克、顧城、海子等著名詩人,都相當於時代巨星。各大詩歌節的門票,永遠都被一搶而光。
與此同時,小說浪潮也如大河出川。
西方的瑪律克斯、卡夫卡、加繆、薩特等,大量湧入書店,青年人冒大雪通宵排隊,就為買一本小說。受西方文學啟蒙,他們也紛紛捉筆創作。
從傷痕、先鋒到尋根文學,湧現了莫言、余華、蘇童、劉震雲、王安憶、王朔、阿城等大批好作家。成名前,他們多是農民、工人、牙醫、小販,但都憑著創作的熱情和才華,構成文學天空的群星璀璨。
此時全國的文學期刊,也迎來空前的井噴式發展。各地僅省級以上的文學期刊,就達200多種。國家級的文學期刊,南有《收獲》,北有《人民文學》,發行量都高達100多萬份。
中國一直沒有文藝復興,然而我們也可以把80年代,當成中國的文藝復興。
雖然我們沒有像六百年前的歐洲,誕生但丁、盧梭、伏爾泰和彼特拉克。但艺文思潮激湧的80年代,同樣有著那時,一把將人從宗教禁欲中解放的痛快淋漓。
02
80年代的覺醒,是從一封信開始的。
1980年5月,《中國青年》收到一封讀者來信,署名“潘曉”,主題是訴說青年人的困惑。信裏首次提到禁忌的“個人主義”,其中最重要的一句寫道:
任何人,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,都是主觀為自我,客觀為別人。
雜誌將信發表,沒成想一時引發全國熱議,各地來信雪花般撲來,多達6萬多封。關於“個人主義”的討論長達半年多,被稱為“一代中國青年的精神初戀”。
以此為分水嶺,中國青年由內而外,開啟對個性的追求。
那時的個性時尚,是戴蛤蟆鏡、穿喇叭褲,手提答錄機播放港臺歌曲。其中放得最多的,是細緻溫柔的鄧麗君。在當時,人們無不“白天談老鄧,夜晚聽小鄧”。
鄧麗君的歌聲,不再沉迷宏大敘事,關心個體的內心。上海電視臺一比特女編導親口講述,臺裏一個年輕人,每一次聽到鄧麗君的那兩句“不知道為了什麼,憂愁它圍繞著我”時,就淚如雨下。
央視曾以“十億個掌聲”為題,連播三期特別節目,開頭如此評估鄧麗君:
她的歌聲,喚醒了無數被禁錮的心靈。
在80年代,喚醒禁錮心靈的,除了春風般的鄧麗君,還有春雷般的崔健。
1986年,在北京工體的百名歌星演唱會上,崔健的《一無所有》橫空出世。激越如嘶吼的搖滾演唱管道,以及那句“我曾經問個不休,你何時跟我走。可你卻總是笑我,一無所有!”唱出一代人個性壓抑後,强烈釋放的狂野酣暢。
在頌聖時代,中國歌曲裏沒有“我”,最多有個“我愛北京天安門”。而鄧麗君、崔健再次讓人們知道,在80年代的字典裏,“我”這個字,依然頑石般地存在。
03
80年代,年輕人也恢復銳氣,敢於藐視權威。
1984年底,學者黃子平參加文學活動。晚上編輯李陀到他房間串門,見他正在那燙脚,膝上放一本書,邊搓脚邊看。問:看的什麼書?黃子平答:《管錐編》。
《管錐編》是錢鍾書的古文筆記體著作,全書130萬字,是學者公認的難啃,讀此書無不正襟危坐。李陀吃驚地說:你就這麼洗腳的時候看《管錐編》?
黃子平笑笑,說:這書洗腳的時候看,最合適不過。
還有一次,詩人食指參加文學活動。結束後,幾比特領導大擺官威,指名要他來合影。他看這副架勢,直接扭頭就走,說“切,我又不是領導,為什麼要配合!”
那年頭,知識份子可以誰都不鳥,也可以敏銳鋒利、口誅筆伐。
80年代初,一比特叫馬北北的25歲女記者,剛進《中國青年報》報社,獲得一條檢報。被檢報的對象,是商業部的部長。內容是他搞特權,在高級飯店吃霸王餐,費用相當於普通幹部月薪,但付的錢還不够買一碗湯。
馬北北證實舉報屬實,直接寫成披露文章《敢於向特權挑戰的人》,同事看過,倒吸一口涼氣,提醒她“這可能是要毀前程的文章”。馬北北就回了兩個字,“不怕!”次日,文章發表在《中國青年報》頭版頭條,劍指權威,舉國譁然。
還有某次大會,鄧小平在會間吸烟,一比特女記者上去遞了個紙條,寫道:
今天是世界戒烟日,請不要抽烟。
還有某次工作會,與會官員紛紛睡覺,一比特攝影師無法取景,直接將眾人睡態拍下,標題取道:《工作會竟成了睡覺會》。
至今,我們仍喜歡那時青年的姿態,睥睨權威,如火烈烈。
04
80年代,也是理想主義和商業,最相容的時代。
1982年,央視開始籌拍《西遊記》。整個劇組只有一臺攝影機,卻為取景走遍全國19個省。當時六小齡童每集片酬,只有70元,全劇拍完,歷經17年。最終,這版《西遊記》創造播放神話,累計觀看130億次。
一次節目中,主持人問導演楊潔:為什麼幾乎沒有人吐槽82版的《西遊記》?
楊潔說:因為我們是在搞藝術,我們沒有為錢,沒有為名,沒有為利。
無獨有偶,那時候誕生的神劇,還有《紅樓夢》。
1987年,《紅樓夢》在央視播出,一時天下無人不識“林妹妹”。
“林黛玉”的演員叫陳曉旭,為演好角色,長年生活中一餐一飯、一顰一笑,皆和角色融為一體。《紅樓夢》拍完後,她因對“林黛玉”用情太深,竟再也無法飾演別的角色,索性退出演藝圈。
後來別的演員問陳曉旭:為什麼現在的演員再難像你一樣,這樣演活一個角色?
陳曉旭說:因為沒有人願意拿自己的一生,來真正投入給一個角色。
這麼多年過去,中國影視業突飛猛進,從資本到特效水准,完全碾壓80年代。但是從藝術水准上來說,卻從未超過那時的《西遊記》《紅樓夢》。原因無它,用錢、用科技,永遠比不過用心、用時間。
作家徐星曾說:80年代,是中國理想主義最濃烈的時代。
那時不僅是詩人、作家在以夢為馬,即便操持商業的人,也同樣堅持理想主義。他們雖在製造娛樂,卻絕不生產速食。為將事情做到極致,可以不惜投入一生。
05
80年代之所以美好,還因為那時的人,簡單溫暖,至真至性。
80年代期間,編輯顧曉陽的家在北京站旁邊,常有人來借住。一天晚上,滿臉鬍子的馬原,經朋友介紹走進來。顧曉陽得知他是小說家,拿出自己的小說給他看。馬原一看,直接說:
你的小說觀念落後一百多年!
顧曉陽一聽不服,和他辯論起來。激動時,兩人互相漫駡、攻擊或讚美。吵到肚子咕咕叫,並肩出門。顧曉陽賣了手錶,凑頓飯錢,請馬原喝酒,接著大吵。
那時的人,幾杯下肚,無話不談。朋友相交,無不率性。
1985年,作家的阿城的家,號稱“北京會館”,每天有各地文友來訪,絡繹不絕。他好用掛麵接待,最多一天下麵16次。有時離家幾天,直接在窗上留字:出門了,幾日回來,鑰匙和掛麵在老地方。
那時畫家朱新建,常去他家刷夜,兩人交談甚歡,徹夜不眠,最高紀錄一天暢談18小時,聲音全啞。後來阿城寫出《三王》大火,背了滿滿一書包錢,街上碰見朱新建,隨手拿了兩摞給他。朱新建問,我為什麼要你的錢?阿城直接說:
這麼多錢,我一個人怎麼用得完?
那時的人,交往也熱烈。校園裏,大家一起讀詩、喝酒、抱頭痛哭。清華、北大的操場,校園歌手常聚,數十個學校學生前來茬琴,輸的當場把吉他砸得稀爛。
那年頭,學生可以在深夜踹開老師的門,就因為看了一本書激動得失眠。男生可以為給穿波西米亞長裙的女老師,買一副隱形眼鏡,去組織俱樂部賣酸嬭。女生也可以把一個月的飯票分成兩半,一人一半,分給最崇拜的流浪歌手。
在攝影師任曙林的眼裡,80年代是一個世紀中唯一凸顯乾淨的年代。
1984年,任曙林在北京171中學,拍下一張《下過雨的操場》。色調幽藍,一個穿白裙的女孩左手拿書,趟水而過,身後的水窪,映出清秀倒影。
歌手老狼特別喜歡這張照片,多年後再仔細端詳,發現角落裏,竟還有一個穿著白襯衫的男孩。他說:我當時熱淚盈眶。瞬間覺得那就是我。
06
我曾以為80年代是上個世紀的故事,很古了,誰還有興趣?
可是出乎意料,每隔一段時間,關於80年代的懷念,就會像潮汐一般捲土重來。
今年的賀歲檔,52億票房的《你好,李煥英》,我們也正是隨著女主人公穿越回到了80年代,在那些平常的日子,感受到一段段閃亮的記憶。
實際上,80年代是個不成熟的時代,無論是社會建設、經濟還是文化,都無法與當下相比。但是,它年輕、真誠,富有朝氣,充溢著理想主義。
而這些,如今離我們,已經越來越陌生。
就像頭髮已花白的北島,在詩中寫道:
那時我們有夢,關於文學,關於愛情,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。
如今我們深夜飲酒,杯子碰到一起,都是夢破碎的聲音。
歸根結底,我們之所以懷念80年代,是懷念那個時候思想的解放,證明了任何封印,都禁錮不了思想。是懷念那個時候人性的覺醒,將每個人的渴望喚醒,將每個人的尊嚴啟動。
也是懷念那些五彩斑斕的詩歌、小說、音樂、影視等,對走出苦難的民族的人道補償。也是懷念那個時代,年輕人的獨立思考、勇敢真誠、追逐理想的信念,是如此的可貴。
我們之所以懷念80年代,是因為那是一場溫柔的反叛。不是創作者在反叛,而是閱讀、聆聽、討論本身就是一種反叛。這種反叛,不同的人群反應不同,底層如岩漿湧動,上層內心依然烦乱。
其實對精神文明的寬鬆,就是對老百姓的寬厚。
告別了80年代,我們迎來一個喧囂和浮躁的時代,一個光怪陸離的時代。
我們遺憾的是,80年代就像一瓶打開的汽水,氣息湧動,但轉瞬散盡。更遺憾的是,80年代雖美好,卻只如曇花一現。竟以如此短暫的管道,一去不復返了。